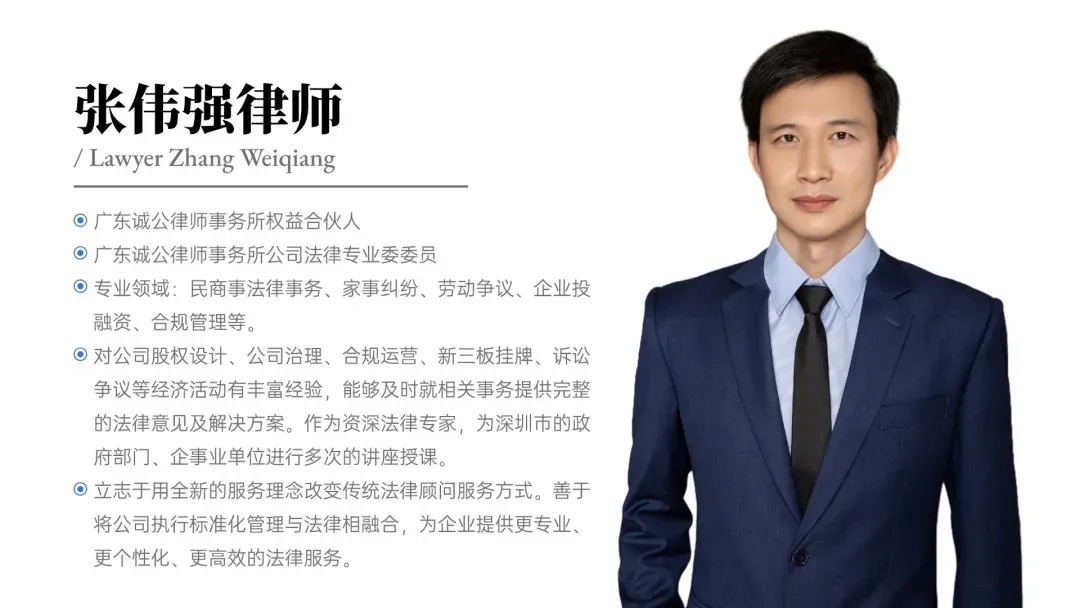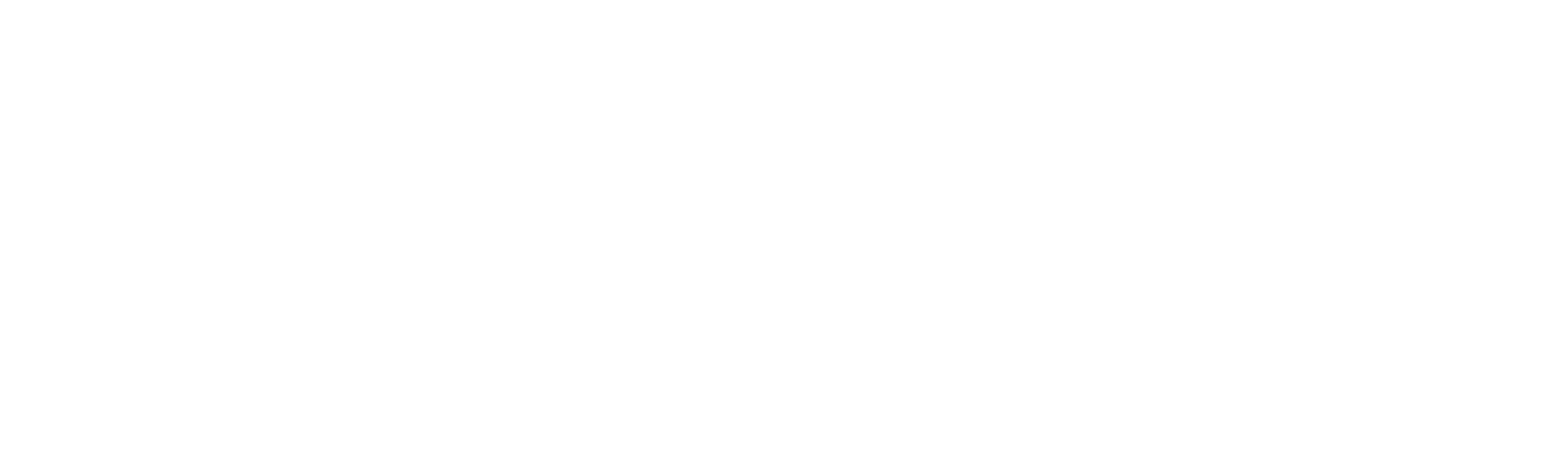本期涉港家事研究正式步入黄金领域一涉港继承深港渐无界,家事仍有别!
大陆继承上,男女平等、继承人范围与顺位在香港是否适用?
题目1
真假养子分辨术
▄▊攻防观点
1.原告人的申请
於 2018 年 9 月 18 日向被告人發出本案的傳訊令狀及申索書,申請撤銷被告人的管理書。
2.被告人的申請
基於他的聲稱,即 1962 年 8 月 19 日在一項領養儀式中吳秀英將他領養,成為吳秀英及吳金泉死後的兒子,而作為吳金泉的唯一在生的男後嗣及吳澤祥的兄弟,他是唯一有權繼承吳金泉的遺產和唯一有權繼承吳澤祥的遺產包括該土地。
3.被告人反申索
要求法庭作出宣稱其為吳秀英及吳金泉合法領養兒子及吳澤祥合法領養兄弟,而因此為唯一有權繼承吳金泉及吳澤祥遺產的人。
▄▊法院观点
1.关于举证责任分配
被告人在他結案陳詞中對原告人結案陳詞作出詳細反駁及聲稱 “原告人未能提供收養儀式中的十位出席者的不在場證據以否定該次收養儀式及午宴的存在”
但被告人似乎誤解了法律,有關領養儀式及中國習慣法,被告人的案情是 (1) 他被領養,因此 (2) 他是唯一有權繼承吳金泉及吳澤祥的遺產的人。舉證責任在於被告人,即被告人須提出足夠証據令本席接納他的案情。
上文已提及被告人最後沒有傳召任何證人可證明他所描述的領養儀式及設宴確曾發生過,也沒有呈交他所指的領養文件。
2.关于証人陳述書
如有證人於審訊中缺席,除非法庭另有命令,該證人的陳述書將不被法庭接納為證供。
被告人並曾呈交一份中國法律專家 WEJEN CHANG (張偉仁教授) (“張教授”) 的意見書,被告人在本案中一直沒有申請法庭命令准予他存檔中國法律專家的意見書,因此本席不接納張教授為本案的專家証人。
本席認為被告人不是一位可信及可靠的証人。本席不接納被告人的証供。本席裁定他所描述的領養儀式及設宴沒有發生過。
3.法律上收养事实是否生效(习惯法的适用)
與適用於香港的中國習慣法的其他領域一樣,中國習慣法(风俗习惯)領養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養父母來自那個地區的習俗。
香港法院過去只能根據代表當事人的專家發表的意見,根據各自的事實處理每一宗案件。
即使被告人被领养(被告人有亲生父母),尤其是在沒有專家證據的情況下,領養和繼承的中國習慣包含許多法院無法解決的複雜問題。
4.不論如何,正式領養繼承人必須公開進行
法庭判定領養儀式收養儀式必須公開,邀請所有客家血統的親朋好友,向客人發出正式的邀請卡,說明儀式目的和被收養男孩的名字。在 Re Estate of Lucien Wong 一案中因儀式沒有公開,所以不構成有效的領養儀式。
本席裁定即使有如被告所描述的領養儀式及設宴,被告人不能成立聲稱的領養儀式是充分地公開,及被告人不能成立聲稱的領養儀式是有吳秀英全家人的認知。
除非得到全家人的認知,否則永遠不會構成被領養。
5.養子不能從多個家庭繼承遺產
在本案中,被告人實際上是通過轉讓得到他生父的其餘遺產,其亲生父亲兩位遗产管理人視被告人為他生父其餘遺產的受益人。
结论:
在考慮了所有証供及証據後,本席重申被告人不是一位可信及可靠的証人,本席不接納他的案情及裁定被告人所描述的領養儀式及設宴沒有發生過。本席裁定被告人並非吳秀英在吳金泉去世後被領養的兒子。
由於被告人申請管理書是基於他為吳澤祥的合法領養兄弟。他此基礎不能成立,因此授予被告人的管理書應被撤銷,及本席拒絶宣稱被告人為吳金泉及吳澤祥遺產的唯一繼承人。
▄▊律师解读
1.遗产管理书需要向高等法院遗产管理处申请,缺乏足够物证需要三个以上的人的誓章(包含法律专家意见)。
2.养子不能从多个家庭基于子女身份继承遗产。
收养有事实收养,收养仪式必须公开举行,是否有法律上的效力,取决于专家意见的支持。
3.专家誓章VS普通的证人陈述书。
证人陈述书需要出席庭审才可能被法院认可。
专家誓章在遗产管理处被认可,但在法庭上因该专家缺席庭审未被法院接受。
▄▊案例原型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2018 年第 21 號
HCAP 21/2018 [2022] HKCFI 1175
案由:遺囑認證訴訟
题目2
撤销遗产管理书
▄▊攻防观点
1.原告人
原告人认为父亲遺囑以書面訂立,由立遺囑人(即死者)簽署,看來死者是欲以其簽署而令該遺囑生效的;死者也在兩名同時在場的見證人劉律師和吳女士面前作出簽署,因此該遺囑顯然是符合《遺囑條例》第5(1) 條的規定的。所以原告人要求法庭撤銷被告人的遺產管理書,把父亲的遺囑認證書授予原告人。
2.被告人
第一被告人指原告人從沒有威嚇或不當地影響死者簽署遺囑,但她指原告人太太曾作出相關的威嚇。以及,表示如果當初原告人於死者逝世後適時披露死者的遺囑,她是不會反對的,而這宗官司亦無需開展。她說原告人特意等龐女士死後才披露遺囑,時間上很有問題。
第二被告人指死者的該遺囑與龐女士的遺囑互相矛盾,因為他們五兄弟姊妹明明是同意要把死者的遺產全部納入龐女士名下的。以及,指出死者如果真的曾作出口頭指示的話,這種口頭指示是應該寫在該遺囑內的。
第一、二被告人反對,因她們認為應出售該住宅單位,並按照龐女士遺囑的意思把售樓的得益平均攤分給五兄弟姊妹。且指稱原告人沒有適時披露死者的遺囑及申請成為遺囑執行人,實在是放棄了身為執行人的權利 。
▄▊法院观点
1.法庭总结主要爭議事項
(1) 死者的遺囑是否在法律上有效及是否應被法庭認證,換言之,該遺產管理書是否應被撤銷;及
(2) 被告人的反申索(包括控訴原告人侵佔該住宅單位引起的租金損失、雜費支出、精神及心理創傷等損失)能否成立。
第一被告人指原告人從沒有威嚇或不當地影響死者簽署遺囑,但她指原告人太太曾作出相關的威嚇。
2.法庭讨论部分
本席同意原告人的陳詞,從劉律師、吳女士的證供,我們看到死者妥善簽署了該遺囑,看來他是欲以其簽署而令該遺囑生效的。他在兩名同時在場的見證人(劉律師和吳女士)面前簽署該遺囑,而劉、吳兩人亦在死者面前作見證並簽署該遺囑。劉律師的證供亦顯示死者確具備正常的精神狀態和神智訂下、簽署該遺囑,他是清楚知悉和同意該遺囑的內容才簽署的。两人絕大部分的證供並沒有受到第一、第二被告人的爭議。即使在盤問之下,她們的證供並沒有受到任何動搖。
本席同意,從劉律師和吳女士在庭上作供的表現可見,她們二人對所肯定的事情都能堅定說出,盤問之下亦不受影響。她們對不確定的事情亦坦白告知法庭「不記得」,證供合符常理。本席信納她們的證供,並裁定死者的遺囑妥為簽署、他有能力訂下遺囑;及他知悉和同意該遺囑的內容,因此該遺囑是有效的。
本席同意原告人的陳詞,從原告人的證供,我們看到死者屬意把自己的兩個物業分給三名兒子,當中並不牽涉任何威嚇或不當影響死者意願的成份。因此,說死者簽署遺囑是受到威脅或不當影響,以致不自願地簽署該遺囑,是沒有事實或可信證據支持的。
本席同意,蔡振圖的證供清楚顯示死者立遺囑後心情愉快,回家時還叫蔡振圖以後安心住在該住宅單位。由此看來,死者並不是帶著被威脅、壓迫或不自願的心情去簽立該遺囑的。
本席同意,事實上,不論原告人在死者抑或龐女士死後才披露死者的遺囑也好,死者遺囑的內容是一模一樣,沒有不同的。
本席同意,所有的證供都顯示死者是自願和妥當地簽署該遺囑的。本席裁定,應讓該遺囑以嚴謹的方式得到認證,並授予原告人遺囑認證書。與此同時,被告人一方的遺產管理書應予撤銷,因為這份遺產管理書發出的時候,法庭並不知道死者原已立下遺囑。
3.法庭命令
本席判令原告人對第一、第二被告人的申索得直,並頒令如下:—
(1) 撤銷日期為2007 年11 月5 日的遺產管理書;
(2) 死者的該遺囑以嚴謹的方式認證,原告人獲授予遺囑認證書;及
(3) 原告人獲授予死者剩餘遺產的遺產管理書。
本席撤銷第一、第二被告人在本案中的反申索。
▄▊律师心得
通过本案例的学习,在律师行订立遗嘱的惯常程序有6个步骤:
(1)律师会见立遗嘱人,向立遗嘱人索取指示或所有资料;
(2)律师草拟遗嘱;
(3)律师向立遗嘱人解释遗嘱内容,确认立遗嘱人明白且同意遗嘱内容;
(4)见证人再次向立遗嘱人解释遗嘱内容,确认立遗嘱人明白且同意遗嘱内容后,立遗嘱人再签字;
(5)立遗嘱人签字后,2名及以上见证人再签字;
(6)律师行复印遗嘱做记录,遗嘱原件交立遗嘱人保管;
如对遗嘱提出质疑,可从三个方面举证推定:
(a)遗嘱是否订立?
(b)李遗嘱人是否有能力订立遗嘱?
(c)立遗嘱人是否知悉并同意遗嘱内容?举证原则是谁质疑谁举证。
▄▊案例原型
案件編號2014年第20號。
题目3
遗嘱认证诉讼局限於誰人應獲授予申請遺產管理權,不处理遺產分配的爭議
▄▊攻防观点
1.呈请人(女方)
(1)第一個部份,是源於男方想購買一部私家車用作家庭使用一事引發
欲購買的私家車價值大約是港幣 40,000 元左右,而牌費、保險、及起初的油費和停車場費用,大約需要港幣 10,000 元。
女方大約是在 2015 年 1 月左右向財務公司總共借了港幣 50,000 元,並交給男方用作支付購買私家車的用途,並由男方負責還款。
男方在 2015 年 1 月 30 日正式為該私家車的登記車主。女方指出這個借贷尚有借款本金及手续费40,542 元未偿还。
(2)第二個部份就是女方的嫁妝,女方指出她發覺她的嫁妝,不翼而飛
後來她發現男方的一張當票,她才知道男方拿了她的嫁妝典當了港幣 11,000 元,女方要求男方歸還這個款項給她。
(3)第三個部份就是關於寬頻上網違約的費用,女方要求男方賠償港幣 4,500 元。
(4)第四個部份就是過去的日子裏男方有向女方借款,最終尚欠女方港幣 2,000 元,女方要求男方歸還這個數目。
2.答辩方(男方)
(1)男方指出買入該私家車的錢,是他自 2013 年年初開始,由他每月薪酬內儲起港幣 1,500 至 2,000 元,儲蓄了兩年後,他便用這筆積蓄來購買私家車。
男方指出在2015年11月初的時候,他把這一部私家車賣掉,原因是他腳傷後,不能長時間工作,以致收入不如以往,沒有多餘金錢來支付車輛每月停泊之用,及他日常生活開支亦出現困難,所以便把私家車賣掉,來換取金錢維持往後的幾個月的生活開支。他亦指出,該部私家車賣出所得的金額是港幣 25,000 元。
(2)男方否認拿了女方嫁妆,並向女方指出會否是男方的哥哥取去,女方找了大約兩個月後,便沒有再理會此事。
(3)男方指出,當時男方叫女方搬走的時候,男方已叫女方把寬頻線也搬離男方的居所,因為男方並不需要這個服務。
(4)男方否认借款。
▄▊法院观点
1.法院认为
(1)男方應否償還女方港幣40,542元
关于關於男方的說法,主要有三個重點:
A.就是在 2015 年 1月之前的過去兩年間,他每月都有儲蓄港幣 1,500 至 2,000 元。
B.就是 2015 年 1 月之後,男方除每月給女方港幣 10,000 元用作生活費外,他還會額外給女方港幣 5,000 元用作儲蓄之用。
C.就是 2015年 1 月之前,男方有買各種不同的禮物給女方,男方指出這表示他的經濟狀況良好,並且支持他有能力儲錢的說法。
2.法院认为
關於第一點,在 2014 年 3 月 5 日的 WhatsApp 對話中,當時女方指出男方欠女方港幣 2,000 元分 4 個月還,每月還港幣 500 元。
若然男方真的有如他所說在該段期間每月都有儲蓄並且放在家裏,當時沒有理由會欠女方這個數目,而且還需分期歸還。
关于第二点和第三点,根据庭审男方的證供可見,男方的證供不盡不實,而且前後矛盾,亦不合情理,因此法庭认為男方是不誠實及不可靠的證人。因為家庭每月的開支是需要港幣 10,000 元左右,而男方亦知道這個數目,所以男方多付的金錢正好是用在每月還款之用。
由於女方沒有能力償還欠款,而這亦是男方的責任,男方需归还女方款项。
(2)男方應否償還女方港幣11000元
法院认为:
女方在庭上的證供指出,男方每月给予女方生活费1万元至1.2万元。在 2015 年 1 月的時候,她並沒有再打算追究典当嫁妆這件事,所以她亦願意為男方借錢買車。既然女方與男方關係良好之時,已不打算追究這筆款項,而即使金頸鏈是屬於女方的嫁妝,這亦是家庭資產的一部份,男女雙方應共同擁有這物品,加上男女雙方共同生活期間,男方一直都有給予女方生活費,所以本席認為女方不應再向男方追討此筆款項。
(3)男方應否償還女方港幣4,500元
法院认为:
女方指出,當時她向男方的哥哥查詢,問他們用不用這個服務,因為女方媽媽的居所,已有寬頻服務,不能再裝多一條寬頻線,女方指出待她找到其他合適的地方搬遷安裝這一條寬頻線的時候,男方已經令到寬頻線服務中止。
根據女方的證供顯示,本席相信是女方沒有處理好繳費一事,才會導致服務停止而毀約,所以不應向男方追討此筆款項。
(4)男方應否償還女方港幣2,000元
法院认为:
至於尚欠女方港幣 2,000 元一事,女方指她在 2015 年 5 月或 6 月左右,亦有提過男方需要歸還女方港幣 2,000 元。
事實上本席認為,男女雙方在生活期間,男方給女方生活費作家庭開支之用,有時女方又給回男方一些金錢,這些來來回回的金錢交往,都不應當作是一方借錢給予另一方看待,因為數目都不是多的數目,若然男方支付了該月的生活費,有時女方需要給回男方一些錢,這些金錢,無論是女方省下男方給予她的生活費,又或是她照顧男方哥哥女兒的看顧費,都可算是來自家庭的積蓄,所以亦應該是大家可以共同享用的金錢,故此關於女方這項要求,本席認為男方無須支付。
▄▊心得体会
法院認為法庭審理附屬濟助問題時,應遵從下列 4 大原則和 5 個步驟。
4 大原則是:
(1)第一個原則是:法庭須考慮审理目的是要達至在雙方之間公平的資產分配;
(2)第二個原則是:公平這個概念表示要排斥一切性別或角色的歧視;
(3)第三個原則是:為了消除潛在的歧視和確保公平,法官就如何分配資產有初步構想時,應該以“平均分割準則”檢查這些構想,必定要有充分和清楚表達的理由才應該不依從這準則;
(4)第四個原則是:法庭不應讓任何人試圖費錢耗時去審查某段失敗婚姻的往事。這樣的審查往往徒勞無功,且很可能大大消耗雙方(和法庭)的資源,以及增加敵意和阻礙和解。
5 個步驟包括:
(1) 第一步(辨清資產)─ 法庭在行使酌情權時,首個步驟是確定與訟每一方在聆訊日之時的經濟資源。具體來說,法庭必須顧及每一方「擁有的或在可預見的將來相當可能擁有的收入、謀生能力、財產及其他經濟來源」。這個步驟的目的,是在顧及每一方的所有實質負債下,計算出該方的淨經濟資源;
(2)第二步(評估雙方的經濟需要)─ 法庭繼而要評估雙方的經濟需要。在通常情況下,可供動用的資產均不足以同時滿足雙方在離婚後的需要,因此運用第 7 條的程序往往到此為止。假如資產有限,則雙方或不能達致互不拖欠的清楚了斷,法庭亦可能要下令其中一方定期向對方支付款項。就此而言,法庭往往要考慮每一方的生活水平、年齡及任何殘疾。法庭應寬鬆地理解雙方的需要,而在資源容許的情況下,雙方的需要應設定於等同他們在婚姻有效期間所享有的生活水平,並因應涉案所有情況而靈活地評估;
(3) 第三步 ─ 決定運用平均分享原則;
(4) 第四步 ─ 考慮有沒有充分理由偏離平等分配原則;
(5)第五步 ─ 作出裁決。
▄▊案例原型
香港特別行政區區域法院婚姻訴訟編號2015年第3049號
FCJA 3049/2015裁決
案由/申请类型:附属济助
题目4
遗嘱认证诉讼
▄▊背景
本案是一宗争产官司。
案中死者邓忍先生于1992年 6 月去世,生前并未立下遗嘱。
邓忍先生与本案原第一原告人罗好女士生有一名儿子,即本案第二原告人邓旭辉先生。
本案在 1994 年提出时,罗好女士还健在。
不幸,罗好女士在 2002 年过身。其遗产在本案之利益由其亲生儿子邓旭辉先生代表。
邓忍先生亦与本案第一被告人朱艳芬女士生育6名子女,即本案第二至第七被告人。
▄▊争议焦点
根据1993年生效的《父母与子女条例》(香港法例第 429 章)第 3(1)条,无论「婚生」或「非婚生」子女皆有权继承已故父母未立下遗嘱处理之遗产。然而,邓忍先生在该条例生效之前,已于1992年6月过身,该条例对本案并不适用。
因此本案是确认谁才是邓忍先生唯一合法妻子,从而确认谁有权继承邓忍先生遗产问题。
▄▊攻守观点
1.原告人
邓忍先生早于1931年11月在中国内地与罗好女士,根据中国旧式婚姻( Chinese customary marriage),谛结婚盟。而根据专家意见,婚礼仪式亦符合当时在内地沿用之《民法》第四篇(亲属)内关于婚姻之条文,尤其是第九百八十二条有关婚姻仪式方面之规定。故根据当时内地生效之法律,为有效之婚姻。
如果邓忍与罗好适用内地法律结婚,又从未正式解除婚姻。那么1942年邓忍就无身份与朱艳芬结婚,罗好才是唯一合法妻子;如果1942年邓忍先生居籍在香港,则《民法》不适用于身居香港的邓忍先生身上,那么朱艳芬是后妻,罗好、朱艳芬及他们各自的子女都享有继承权。
2.被告人
邓忍先生与朱艳芬女士于1942年在香港「结婚」。就仪式(formality)方面而言,符合《婚姻制度改革条例》(香港法例第178 章)内关于「新式婚姻」(modern marriage)之规定。只要结婚双方有结婚之身份(capacity to marry),则根据条例第 8 条,该婚姻实属有效。
▄▊法院观点
案件关键取决于罗好女士声称之 1931 年内地婚姻是否真实发生及为有效,举证责任在原告人一方。再者,关于这类前后两段婚姻的情况,案例显示,若其后的一段婚姻之法律 手续或形式(legal formality)方面并无疑问,则法庭会倾向于维系第二段婚姻,而假设第二段婚姻(亦即是现存之婚姻)为有效;除非有「决定性」之证据(decisive evidence),推翻这个假设。
当然,若第一段婚姻能有足够证据支持,便可构成决定性之证据推翻有利于第二段婚姻之假设。但若第一段婚姻之存在或合法性令人存疑(doubtful marriage),则并不构成足够之决定性证据,去推翻这个有利于第二段婚姻之假设。
在考虑整个案情,尤其是上述之因素后,根据民事举证之 责任及标准,本席裁断原告人一方,并未能证明罗好女士确曾在 1931年与邓忍先生在内地成婚,是他的合法妻子。
本席强调,本席之裁断是基于审讯时获接纳之证据、举证责任及标准而作出,尤其是在罗好女士已去世,不能亲身出庭作证的情况底下作出。至于事实之最终真相如何,并不是本民事法庭所能作出裁断的。当事人(即邓忍先生及罗好女士)已作古,真相可能永远不能知晓。
基于本席上述之事实的裁断,本席进一步裁定,第二原告人邓旭辉先生并非邓忍先生之合法或婚生儿子,并无权利分享邓忍先生之遗产。
另一方面,本席裁定朱艳芬女士为邓忍先生唯一及合法之妻子及遗孀,她与邓忍先生之6名儿女,即第二至第七被告人为他们之合法及婚生儿女,他们 7人均有权根据《无遗嘱者遗产条例》(香港法例第 73 章)分配邓忍先生之遗产。
▄▊律师心得
1.根据《父母与子女条例》及《无遗嘱者遗产条例》,自1993年起,香港已通过修法确认非婚生子女的法定继承权。这类子女无需通过法院声明即可继承生父或生母的遗产,前提是亲子血缘关系需在生前或法律程序中获得确认。
2.香港在1971年10月7日正式废除一夫多妻制,全面实施一夫一妻制。
▄▊案例原型
HCAP 6/1994
题目5
涉港遗产继承案件中的遗嘱效力认定与遗产分配
▄▊攻防观点
1.原告人(曹健强、LO MAY YUK)主张
(1)主张 2011 年 4 月 9 日死者卢光在叶谢邓律师行签署的中文遗嘱合法有效,请求法院以严谨法律形式确认该遗嘱效力,并在符合遗产承办处要求后,授予自身死者遗产的遗嘱认证。
(2)主张香港爱信道 33 号东涛苑 A 座 11 楼 4 室(东涛苑物业)在所有关键时间均属死者遗产,且根据遗嘱,自己与李俭卿(原告人母亲)应作为该物业联权共有人,同时平均继承死者清付债务、税费等后的全部动产与不动产遗产。
2.排除干扰与权益保护请求
主张自身与李俭卿长期独占用有东涛苑物业,被告人多次干扰或促使他人干扰物业使用,请求法院作出禁止令,禁止被告人及其代理人、佣工等侵入或干扰原告人及李俭卿对该物业的私有、独占用有。
(1)被告人(LO MAY YUK)抗辩
否认 2011 年遗嘱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主张遗嘱存在 “不合常理”“程序瑕疵”,具体包括:叶谢邓律师行未向死者提供法律重点参考,遗嘱缺乏足够医护见证人,未提及死者身后事安排,违反死者对物业的原有安排,遗漏对被告人(死者女儿)生活照顾的承诺,遗产继承人(原告人及李俭卿)诚信与行为不可靠,赠予内容不合常理。
质疑死者立遗嘱时的行为能力,主张死者 2010 年 10 月因头部受伤接受脑部手术(清除脑内血肿),康复期长达一年,2011 年 4 月立遗嘱时可能仍受术后影响,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提交死者 2010 年 10 月至 2011 年 2 月的医疗报告(入院记录、脑部 CT 扫描结果、出院小结等),佐证头部受伤与手术事实。
▄▊法律适用
确立遗嘱效力认定的 “三要件” 举证责任规则:
(1)提呈遗嘱一方(本案原告人)需按 “相对可能性衡量标准”,证明遗嘱 “妥为签立”“立遗嘱人有能力订立遗嘱”“立遗嘱人知晓并同意遗嘱内容”;
(2)明确若遗嘱表面合理且已妥为签立,法院推定立遗嘱人具备行为能力,反驳方需提供充分证据推翻该推定。
细化立遗嘱能力的认定标准:
(1)指出若遗嘱由独立且经验丰富的律师准备,律师已向立遗嘱人宣读解释内容并确认其理解,可作为立遗嘱人具备能力的重要指标(但非终局性);
(2)强调法院需结合全部证据(含非医疗证据)及司法常识评估行为能力,不能仅依赖医疗报告。
补充 “立遗嘱人知晓并同意遗嘱内容” 的推定规则:
(1)若遗嘱妥为签立且立遗嘱人具备能力,法院可推定其知晓并同意内容;
(2)若遗嘱由独立律师专业准备且律师已解释内容,该推定的证明力更强,反驳方需提供相反证据方可推翻。
确立 “利益相关者准备遗嘱” 的警惕规则:
(1)若遗嘱由受益人(或与受益人有关联的人)写成或准备,法院需对遗嘱效力保持警惕,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遗嘱体现立遗嘱人真实意愿,否则不予认可;
(2)本案中被告人虽未直接主张遗嘱由原告人准备,但质疑原告人诚信,法院需结合该规则审查遗嘱订立过程的独立性。
▄▊争议焦点
1. 2011 年遗嘱是否 “妥为签立”?
原告人举证:
黄嘉宝律师出庭作证,确认其为遗嘱见证人之一(另一见证人为陈婉明律师),死者在两名见证人在场时签署遗嘱,见证人亦在死者在场时签署;黄律师提交誓章及律师行电脑记录(含遗嘱草拟人、2011 年 4 月 1 日收费单、确认书草拟人)。
法院认定:
虽黄律师年资较短,但其一贯做法为 “解释内容 - 确认理解 - 安排签署”,且遗嘱文本明确记载解释与确认过程,律师行电脑记录(收费单、文件草拟人)可佐证遗嘱订立的真实性;确认书虽无死者签名,但黄律师确认其为当时准备的文件,结合遗嘱签署的见证人在场情况,认定遗嘱符合 “妥为签立” 要件,满足《遗嘱条例》第 5 条要求。
2. 死者 2011 年 4 月立遗嘱时是否具备 “立遗嘱能力”?
被告人举证:
提交死者 2010 年 10 月 2 日跌倒入院的医疗记录(诊断为 “轻微头伤”,无昏迷)、2010 年 11 月 8 日因 “慢性硬膜下血肿” 接受 “钻孔引流术” 的手术记录、2010 年 10 月至 2011 年 2 月的脑部 CT 扫描报告(显示 2011 年 2 月 21 日血肿体积减少,仅少量残留),主张手术康复期长达一年,2011 年 4 月死者可能仍存在认知障碍。
法院认定:
医疗报告显示死者 2010 年 11 月手术后恢复顺利,2011 年 2 月血肿已基本清除,8 月覆诊时状态正常;结合死者术后仍能驾驶小巴(需具备正常认知与反应能力)的事实,认定被告人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死者曾受伤手术,但不足以证明 2011 年 4 月立遗嘱时存在行为能力缺陷;依据 Re The Estate of Lau Heung 案规则,结合黄律师 “未察觉死者有认知问题” 的证言,推定死者具备立遗嘱能力。
3. 死者是否知晓并同意 2011 年遗嘱的内容?
法院认定:
依据 Kwok May Sin Kylie 案规则,黄律师作为独立律师已履行解释义务,且遗嘱内容明确、无歧义,死者签署前有 10 分钟自行阅读时间,足以理解内容;被告人主张 “不合常理”,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死者与子女关系紧密(如无证据证明死者生前向被告人支付赡养费、被告人未安排兄长作证),反而原告人提交的合影、共同居住文件可佐证死者与原告人一家的紧密关系;李俭卿未出庭虽存在瑕疵,但原告人解释其年近 70 且原律师未建议,不足以推翻推定;最终认定死者知晓并同意遗嘱内容。
4. 东涛苑物业是否属死者遗产,原告人请求的禁止令是否应支持?
原告人主张:
提交东涛苑物业的产权登记文件(死者为登记业主),主张物业属死者遗产;提交被告人干扰物业使用的证据(如擅自进入、争执记录),请求禁止令保护自身权益。
被告人反驳:
主张物业为 “祖屋”,由死者以自身积蓄购买,原告人所述 “出资” 无充分证据(如无直接出资凭证),物业应属死者遗产但被告人享有法定继承权;主张自身介入物业是 “维护继承权”,不属于 “非法干扰”。
法院认定:
产权登记明确死者为东涛苑物业的登记业主,被告人未提供证据证明物业为 “家族共有” 或自身享有权益,认定物业属死者遗产;关于禁止令,因原告人尚未取得遗嘱认证,未正式成为物业业权人(需通过 “允许书” 登记),且李俭卿非本案申请人,依据《高等法院规则》第 76 号命令,裁定暂不支持禁止令请求,待原告人完成产权登记后可另行主张。
▄▊他山之石
本案中原告人最终胜诉,关键在于严格依据 Nina Kung 案确立的 “妥为签立、能力、知情同意” 三要件举证:
通过律师见证证言与文件证明 “妥为签立”,通过医疗报告与术后生活证据证明 “能力”,通过律师解释证言与推定规则证明 “知情同意”。
本案中黄律师的参与成为遗嘱效力的关键支撑:
作为独立见证人,其证言证明了签立程序的合法性;作为遗嘱草拟人,其解释义务的履行佐证了死者的知情同意;即使其年资较短,但 “一贯专业流程” 的证明仍被法院认可。
被告人以 “遗嘱不合常理”(赠予无血缘关系者)质疑效力,但法院未采纳,核心原因在于原告人提供了大量事实关系证据(共同居住文件、合影、物业开支凭证),证明死者与原告人一家的紧密关系,使 “赠予无血缘者” 具备合理性。
本案中原告人虽胜诉,但因尚未取得遗嘱认证,法院暂不支持禁止令请求,体现香港遗产诉讼 “程序优先” 的特点:
只有完成遗嘱认证并办理产权登记,继承人才能正式取得遗产权益,进而主张排除他人干扰。
此外,原告人初期未及时存档黄律师誓章,被告人多次以 “身体不适” 申请延期,均导致诉讼拖延,提示当事人需严格遵守《高等法院规则》第 76 号命令的程序要求(如按时提交证据、配合审讯安排),避免因程序瑕疵影响权益实现;同时,在遗产争议中,应尽早通过 “知会备忘录” 锁定遗产权益,防止他人抢先申请遗产管理书。
本案中李俭卿未出庭作证虽被法院指出 “存在瑕疵”,但原告人通过其他证据(如共同居住文件、黄律师证言)弥补了该缺陷,未对判决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而被告人未安排兄长(声称与死者同住至 2005 年)作证,导致其主张的 “死者与子女关系紧密” 缺乏证人支持,成为不利因素。这提示在涉港诉讼中,关键证人出庭虽重要,但并非唯一证据来源,若能通过文件、第三方证言(如律师、医生)等形成证据链,可有效补位证人缺席的瑕疵;反之,若仅依赖主张而无证据链支撑,即使逻辑上 “合理”,也难以获得法院认可。
▄▊案例原型
高院遺囑認證訴訟 2018 年第 42 號
案号:HCAP 42/2018 [2021] HKCFI 1696
审理法院: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
题目6
可否继承父亲妾侍遗产
▄▊攻防观点
1.原告人
原告人指稱死者甘克明(“甘氏”)是他父親的妾侍,因此他是甘氏遺產的繼承人之一,他要求法院委任他作為遺產管理人。
2.被告人
否認甘氏是所稱的“妾侍”,她仍獨身,未有子嗣,而被告人則是甘氏親弟,所以有權繼承遺產,他才應成為遺產管理人。
▄▊法院观点
本案唯一的爭議點是“甘氏”是否原告人父親葉鎮邦的妾侍?
若甘氏是葉鎮邦的妾侍,則根據香港法例第 73 章 《無遺囑者遺產條例》附表 1 中的第(2)(a)(i) 條,原告人葉錦祥及其親妹葉秀瓊乃是甘氏之子女,可以繼承甘氏全部遺產,並且原告人理應可以成為甘氏的遺產管理人。而被告人甘炳光(就算他真的是甘氏的親弟)也無權分享甘氏的遺產。
1.構成夫妾關係的原則
在 1971 年 10 月 7 日以前,以香港為居藉的男士均有權娶妾。
原告人在本案中需要證明以下三件事項
(1)葉鎮邦與甘氏有共同意圖締結成為夫妾;
(2)於葉鎮邦在生時,甘氏被葉鎮邦的正室(妻子)接納為妾侍;
(3)於葉鎮邦在生時,甘氏妾侍的身份被男方的家人普遍承認。
2.原告方证人的诚信
簡彩楊女士、馬麗英女士與葉長椿先生,都是與甘氏和葉鎮邦正室王復幾十年來過從甚密的親戚。
馬麗英是葉鎮邦堂兄的太太,葉長椿是葉鎮邦的堂弟,簡彩楊是王復的親弟婦。
另一原告方證人方漢清女士是甘氏死前七年中身邊的密友、契女。
3.原告人诚实可靠
父親葉鎮邦在1986 年把遺囑的內容告訴原告人,他把部分財產要轉移到甘氏名下的想法(為了怕大兒子不分給弟妹的緣故),在甘氏面前都告訴原告人了。
另一方面,原告人沒有反對父親的意見,並同意父親的做法,可見原告人對“細媽”甘氏的信任與尊重。
原告人說父親娶妾的主意是祖母提出、由母親同意的。甘氏稱王復為“姐”,王復稱甘氏為“妹”。
4.被告人的證供缺乏誠信及可信性
在審訊期間,被告人說了很多難以置信、離奇古怪的事情。
被告人更說從來沒有與甘氏談論過甘氏的婚姻、拍拖的情況,但他卻一口咬定甘氏從來沒有結婚或同居。
這證明被告人是一名極度武斷,並不可靠的證人。
被告自認從 1951 年到 1980 年期間一直都被關在東北遼寧的監獄裏,他承認所有有關甘氏在這段時間裏的消息都是後來他被釋放出來回港後,從家人所認識的人的口中得知的。被告人沒有說是從甘氏的口中得知任何資料的,也沒有解釋那些所謂家人所認識的人是誰。
被告人違反了聆案官在本案頒下的命令,沒有向香港入境事務處申請被告人個人背景的資料,並且在本案審訊時第一次提出了嶄新的藉口,說什麼申請都沒用,因為入境處已經把他的出生證明書與在香港上學的證明書都丟失了,也從來沒有嘗試申請補領,並斷言他的出生證明書應該是給日本軍燒了。
到目前為止,被告人只能拿出甘氏父母的死亡證,但上面沒有被告人的名字,只有甘氏的名字。
被告人在他自稱是甘氏親弟的論據中,嚴重缺乏誠信,而他盲目不斷地否認葉甘之間夫妾關係的證供證據,本席也並不接納。
5.葉鎮邦與甘氏有共同意圖締结成為夫妾
6.葉鎮邦家人對甘氏為葉鎮邦妾侍的承認
7.總結及命令
本席接納:
(1)原告人父親葉鎮邦與甘氏有共同意圖締結成為夫妾;
(2)於葉鎮邦在生時,甘氏被葉鎮邦的正室(妻子)接納為妾侍;
(3)於葉鎮邦在生時,甘氏妾侍的身份被葉鎮邦的家人普遍承認。
頒令如下:
(1)宣布死者甘克明是原告人父親的妾侍;
(2)宣布原告人是死者甘克明的兒子/後嗣;
(3)宣布原告人有權就死者甘克明的遺產,根據香港法例第10章《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內的有關次序申請遺產管理書;
(4)宣布原告人有權就死者甘克明的遺產,根據香港法例第 73 章《無遺囑者遺產條例》第 4 條內的次序承繼死者甘克明的遺產;
(5) 撤銷被告人在本案中的反申索;
(6) 任何一方均可提出申請(Liberty to Apply)。
本席作出暫准命令,本訴訟的訟費由被告人支付原告人(包括保留代決的訟費),若雙方未能就訟費數額達成協議,則數額留待法庭評定。倘若在本判案書頒下後 14 天內並沒有任何更改訟費命令的請求,此暫准命令將成為絕對命令。
▄▊解读与收获
在1971年10月7日以前,香港居藉男士均有權娶妾。与妻子所生子女可以继承妾侍的遗产。
香港法例第10章《遗嘱认证及遗产管理条例》是香港规范遗产继承程序的核心法律,主要规定遗产承办的司法程序、遗产管理人的任命与职责等关键事项。
(1)授予书制度
明确“授予书”(俗称“承办纸”)为处理遗产的法定文件,包括遗嘱认证(有遗嘱时)和遗产管理书(无遗嘱或遗嘱执行人无法履职时)两种形式。
(2)遗产承办处职责
授权香港高等法院设立遗产承办处,负责处理无争议的遗产申请,确保授予书发给合法人士。
(3)遗产管理人规定
若死者无遗嘱或未指定执行人,法庭需按法定优先次序(配偶>子女>父母等)任命遗产管理人。
(4)法律责任
未经法庭授权擅自处理香港遗产属刑事罪行,强调必须通过司法程序获取授予书后才能处置遗产。
香港法例第73章《无遗嘱者遗产条例》第4条是香港关于无遗嘱(未立遗嘱)情况下遗产法定继承规则的核心条款,主要规定遗产在不同亲属关系中的分配方式,具体情形包括:
(1)仅遗有配偶
无子女、父母或全血亲兄弟姐妹及其后嗣时,遗产全部由配偶继承。
(2)遗有配偶及后嗣
配偶先取得50万港元权益(含利息),剩余遗产一半归配偶,另一半由子女平均分配。
(3)遗有配偶但无子女
配偶先取得100万港元权益(含利息),剩余遗产一半归配偶,另一半由父母均分;若无父母,则由全血亲兄弟姐妹均分。
该条款是香港处理无遗嘱继承的直接法律依据,需结合被继承人死亡时的亲属状况适用。
▄▊案例原型
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原訟法庭遺囑認證訴訟2012年第25號HCAP25/2012
案由/申请类型:遺囑認證訴訟
题目7
遗嘱有效性认定的法律原则及构成要件
▄▊攻防观点
原告人卓树贤(女方)诉请:
(1)2010年2月19日订立的遗嘱(“第三份遗嘱”)无效。
(2)第三份遗嘱中死者指定及委派他姐姐,即第一被告人(“罗女士”)及父亲,即第二被告人(罗先生)为遗嘱之共同执行人,而受益人为罗先生及死者的母亲(叶女士)。
▄▊案情简述
死者是於 1963 年在廣東省惠陽縣出生。他和卓女士在1994 年 8 月在香港結婚。
死者為一名工程師,卓女士為一名文員。婚后育有两名女儿,大女兒在 1995 年出生,現 17 歲,及二女兒在 1997 年出生,現 15 歲。
2004年6月开始分居,但仍同住在同一屋檐下。
2006年8月死者申请离婚,理由为双方分居满两年。
2007年1月获暂准离婚,将两位女儿的管养权判给卓女士并並命令死者支付給兩名女兒中期贍養費每月共 HK$5,000。
在 2007 年 4 月法庭命令死者支付兩名女兒的中期贍養費由 3 月 1 日開始加至每月共 HK$6,000。據卓女士所指,死者在支付了約 4 個月女兒的贍養費後就停止付款。
2008 年 4 月 10 日在香港浸信會醫院經掃瞄後被確診患有肺癌。
2008 年 4 月 16 日死者在香港的一間律師行作出他的第一份遺囑(“第一份遺囑”)。委任他的表弟葉先生作為遺產的唯一執行人及兩名女兒的監護人而遺產受益人為兩名女兒。
2008 年 6 月 26 日死者在同一間律師行作出第二份遺囑(“第二份遺囑”)。他在第二份遺囑中廢除了第一份遺囑,並委任羅女士及他妹妹作為遺產執行人及將遺產分為 6 份,父、母、兩名女兒及兩名姐妹各一份。兩份遺囑的見證人分別為律師行的律師及見習律師。
死者是於 2010 年 2 月 28 日逝世,當時未足 47 歲。
死者在逝世前約 9 天,即 2010 年 2 月 19 日,在南山醫院作出第三份遺囑。這也是他所作的最後一份遺囑。
在第三份遺囑中,死者聲明所有以前訂立之遺囑作廢,及指定及委派羅女士及羅先生為遺囑之共同執行人,而遺產的受益人為他父母羅先生及葉女士,平均分配。死者並聲明以香港為永久居留地及遺囑應根據香港法律解釋及辦理。該遺囑有兩名見證人,一位為羅女士而另一位為表弟葉先生。
在死者逝世後,於 2010 年 3 月 26 日家事法庭命令離婚訴訟終止。當時法庭仍未審理卓女士的附屬濟助的申請。卓女士及兩名女兒現時正在領取社會福利署綜援金。
2010 年 12 月 22 日她和兩名女兒在深圳向死者的父母羅先生及葉女士 提出起訴,請求分割夫妻共同財產及死者的遺產。羅先生及葉女士即作出反訴。
最後在 2012 年 2 月 24 日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作出一項判決書確定死者在國內的遺產範圍(“深圳判決書”)。卓女士稱她已提出上訴,現仍在進行中。在深圳判決書中法院曾指出該第三份遺囑為死者“在神智清楚的情況下親筆簽署,合法、有效”。
在香港卓女士也曾就昌盛苑物業提出訴訟,昌盛苑物業的聯名註冊業主為死者的父母即羅先生及葉女士。在死者申請離婚之後不久,卓女士向羅先生及葉女士提出申索指購買昌盛苑物業的資金源自她和死者的共同資產,因此卓女士才是該物業的實質擁有人而羅先生及葉女士只是信託人。
有關昌盛苑物業的訴訟其後在 2009 年 6 月聆訊。當時死者似乎亦曾出庭替父母作證。後在 2009 年 6 月 25 日,高等法院原訟法庭馮驊法官正式宣告卓女士與死者為昌盛苑物業的實益擁有人而羅先生及葉女士只為該物業的信託人 。
在 2011 年 4 月 1 日羅先生及葉女士上訴得直,馮法官的裁決被撤銷。但卓女士繼續上訴,最後終審法庭在 2012 年 11 月 13 日推翻上訴庭的判令並維持馮驊法官的原判。因此卓女士在昌盛苑物業現擁有至少一半的實質權益。卓女士和兩名女兒是一直居住在該物業內。
在 2010 年卓女士在高等法院向羅女士及羅先生就死者另一項在大埔的物業提出訴訟,指她為該大埔物業的全部權益實益擁有人,在 2010 年,卓女士並根據香港法例第 481 章《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在家事法庭作出相關的申請。該兩項訴訟現暫被擱置中。
▄▊争议焦点
高等法院黃健棠聆案官在 2012 年 1 月 26 日所作出的命令中列出各方同意本案的爭議點為如下:
(1) 死者在 2010 年 2 月 19 日簽立第三份遺囑時是否清楚、明白其目的及內容?
(2) 即使死者清楚、明白上述遺囑目的及內容,他是在國內簽立的其形式(formality)是否有效?
(3) 以香港而言第三份遺囑是否有效?
有關法律原則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潘兆初法官在有關招有全遺產一案中曾指出如一份遺囑的有效性被挑戰而挑戰原因為立遺囑人缺乏立遺囑能力及立遺囑人不知道及不贊同其內容,法庭對舉證責任方面是採納以下的方式:
(1) 提呈遺囑的一方是負有“法律或游說”的責任(legal or persuasive burden)以證明及令法庭信納該遺囑為立遺囑人的遺囑,而舉證準則為相對可能性的衡量。 提呈遺囑的一方是須要向法庭證明如下:
(a) 立遺囑人的是有立遺囑的行為能力;
(b) 立遺囑人是知道及贊同遺囑的內容;
(2) 如有一方欲質疑遺囑的有效性,而理由為立遺囑人缺乏行為能力或簽立之時並不知道或贊同其內容,該方是負有證據上的舉證責任(evidential burden)以將其理由作為爭議點。
至於立遺囑人有否立遺囑的行為能力,法庭是須考慮立遺囑人在立遺囑時是否有任何精神、記憶及理解能力不健全。他的記憶能力是必須要健全,即是他可回憶所有有可能成為他的受益人,及他的理解力亦應健全,即他是明白他和有可能成為受益人的血統關係或友誼關係及他們有可能提出的申索。法庭並不須要實際明白記憶或理解的證據。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歐陽法官也曾在另一遺產認證案件中指出真正簽立遺囑的那一刻,立遺囑人必須具有處置財產的健全心智和健全記憶。用以決定立遺囑人是否具有適當的精神上的行為能力的經典測試方法是載於英國 Banks v. Goodfellow 一案中 [1870] LR 5 QB549:-
(1)“要行使這種權力,下述條件是必不可少的;
(2)立遺囑人必須明白他的行為是甚麼性質的行為,和他的行為有甚麼作用;
(3)他必須明白他要處置的財產有多少;
(4)他必須理解和覺察他應該依從的索求是哪些索求。
而且,就末項而言,他必須沒有因心智失常以致他對人的感情受到侵害,或者是非對錯的觀念受到破壞,或者運用固有的官能的能力受到妨礙—— 他處置他的財產時,他的意志必須沒有被精神錯亂的幻覺影響以 致作出他在心智健全的時候不會作出的處置。”
歐陽法官曾指出有一個假定是立遺囑人在訂立他的遺囑時是具有處置財產的健全心智。如果立遺囑人的立遺囑的行為能力受到質疑,提呈遺囑的一方便有責任以相對可能性的衡量去證明立遺囑人是有立遺囑的行為能力。但是,如果遺囑在表面上是合乎理智的,並且證實是妥為簽立,又沒有人提供其他證據,法庭便會推定立遺囑在精神上有足夠能力,並會宣判遺囑有效。
第一爭議點
羅女士及羅先生均出庭作證並確認他們證人陳述書的內容。
羅女士呈交了在 2010 年 2 月 19 日 及 2 月 21 日,分別由兩位南山醫院醫師所作的查房記錄。這兩天的記錄均顯示死者分別在該兩天神智清楚只是精神較差。
卓女士反對羅女士呈交這查房記錄,因卓女士指在醫院檔案中她找不到此記錄及這記錄沒有醫生簽名也沒有前後頁。
羅女士在審訊時曾經顯示給本席查看蓋有紅色醫院蓋章該查房記錄的副本,但羅女士指她因為要向在深圳法院顯示該記錄因此不能將有蓋章的記錄呈交本法庭作為證物。
羅女士是早在 2011 年 3 月 4 日的抗辯書中提及此記錄及其後在文件清單上披露了該記錄。
卓女士有足夠時間去南山醫院調查或獲取有關證據去證明這查房記錄的真實性。
在深圳訴訟中本席看不到卓女士曾質疑此記錄的真實性。
羅女士也解釋了是南山醫院複印了該兩天的醫師查房記錄後再蓋章證名為該醫院的文件。
在考慮了羅女士的證供後,本席接納她的解釋及接受該記錄。
羅女士及羅先生傳召了第三份遺囑的另一位見證人,即死者的表弟葉先生。葉先生簽了一份證人陳述書並出庭作證。葉先生和死者的關係是姑表兄弟也是朋友。他們的關係密切。葉先生告訴法庭在死者逝世之前葉先生曾協助死者處理他有關所有官司的文件。
葉先生是第一份遺囑中的唯一執行人。他指當時他並不知道死者曾委任他為遺囑執行人及兩名女兒的監護人。他是後來替死者整理官司文件在檔案中發現一份遺囑有他本人的名字,及看到他是死者女兒的監護人才詢問死者但當時死者告訴他該份遺囑已取消了。
葉先生聲稱他在 2010 年 2 月 18 日接到死者的電話而死者是用他自己的手機致電給葉先生。死者要求葉先生去找律師替他準備一份遺囑。死者在電話中告訴葉先生他的遺產是平分給他的父母及葉先生及羅女士作為遺囑的證人。死者也曾要求葉先生問律師能否到深
圳去作他的遺囑的證人。葉先稱他沒有相熟律師但看到謝偉俊律師行的廣告便於第二天早上去到該律師行。當時因死者並沒有向葉先生列明資產因此律師行草擬了一份通用的遺囑,內容沒有列出具體財產,只是將名下各處不動產及動產饋贈給死者的父母。
葉先生稱死者在2月18日的來電中曾告訴他羅女士會將她及父母的身份證號碼用電郵發給葉先生。但在該日葉先生結果是沒有收到羅女士的電郵。第二天 2010 年 2 月 19 日葉先生在律師行致電死者,告訴死者他並沒有收到羅女士的電郵。死者告訴他在醫院中他有一部“Notebook”其後會將有關父母及羅女士身份證的資料發電郵給葉先生,但葉先生稱因他當時在律師行,因此不能開啟他的郵箱。最後羅女士發短信給葉先生告知他有關父母及她本人的身份證號碼。
因此,據葉先生所稱,他在 2010 年 2 月 18 日及 19 日和死者兩次通電話。葉先生指死者和他通電話時是神智清楚,雖然說話聲音微弱。
葉先生並告訴法庭在 2010 年 2 月 18 日當死者致電給他時,曾表示想見大女兒。後來葉先生約了大女兒,在 2 月 19 日和她一起到南山醫院。葉先生聲稱當他在 2010 年 2 月 19 日和死者通電話時曾告知死者大女兒會和葉先生一起到醫院。當時死者要求葉先生不要告知大女兒有關立遺囑之事,因死者想避免尷尬因為遺囑中沒有提及女兒。
葉先生稱他和大女兒到達南山醫院死者的病房時因為死者不想女兒看到他簽遺囑因此葉先生和羅女士在死者床傍“遮遮掩掩”。他將遺囑交給死者,死者自己閱讀後就簽名,死者簽後羅女士簽名,後他本人簽名。三人是同時在場簽名的。
葉先生確認死者簽遺囑時“精神可以,雖然說話細聲”。葉先生強調他本來是想要求律師親自到深圳作見證,但律師不願意去深圳。
葉先生指律師行事實上準備了四份遺囑,在兩份上是打上了見證人,即他和葉女士的名字,另外兩份是沒有打上他們的名字以防臨時變換見證人。最後死者是簽了三份,因此其中兩份是有見證人葉先生及羅女士的全名,而另外一份則沒有。簽妥後所有的遺囑全交回死者。
據葉先生所述,在簽完遺囑後,死者曾和女兒傾談一會。之後在葉先生帶大女兒離開之前,死者拿了一張紙,親自寫了一封信,要求葉先生替他寄去家事法庭申請聆訊延期。除了該信件第一行“尊敬的法官”卓女士並沒有質疑其餘為死者的字蹟。
不論如何,本席接納葉先生及羅女士的證供,該信件除第一行外,其餘為死者親筆所寫。
葉先生在審訊中告訴法庭在 2 月 19 日簽妥第三份遺囑,約7日後他曾再去探訪死者,並在 2 月 28 日早上他也曾去探訪死者。
他指在兩日探訪中,死者是神智清醒。他曾詢問死者為何遺囑中只有父母為受益人,因他知道死者之前是很愛錫兩名女兒的。死者向他表示因為這兩年的官司影響到女兒對爺爺嫲嫲的態度不好,並且小女兒曾趕爺爺嫲嫲出家門。
死者向葉先生表達的意思是如果遺產受益人只有他父母,這可能會改善兩名女兒和爺爺嫲嫲的關係,因為他們的關係如改善的話,爺爺嫲嫲可能將來會有些財產留給他們。葉先生知道正在死者名下的遺產不多,及死者是希望他的安排會能改善爺孫的關係而死者認為這對女兒會更好。
另外葉先生在庭上提及死者生前曾和葉先生聯合投資,因此有一筆款項是葉先生須要償還給死者的,但死者吩咐葉先生現在毋須償還,待大女兒 18 歲讀大學時替她支付學費。 葉先生稱他已告知卓女士及大女兒有關此款項而羅女士及羅先生也是知道此事的。葉先生並告知法庭,死者曾告訴他父親曾替他支付了約$100 萬元的醫藥、治療及生活等費用。這也支持了羅先生的證供,雖然羅先生指他花了$200 多萬。
無論如何,本席接納羅先生自約 2007年底死者患病後曾為死者支付很多費用。
據羅女士的證供,死者一直是神智清楚直至 2010 年2月28日下午才開始昏迷。在 2 月 18 日死者致電葉先生立遺囑當日,他還自己手寫了有關父母身份證號碼的便條。羅女士確認遺囑是死者先簽名,隨着她簽名,然後葉先生簽名,三位同時在場。卓女士在結案陳詞中指葉先生和羅女士有關羅女士發出父母身份證的電郵給葉先生的證供並不吻合,因醫院沒有電腦發電郵及羅女士稱她是在家中發電郵給葉先生。葉先生所指的“Notebook”是手提電腦而羅女士解釋該電腦是她帶到醫院給死者使用的。至於葉先生所指沒有收到羅女士在2月18日發的電郵,羅女士解釋這是因為她打錯了葉先生的電郵地址而這在死者的便條上可看到。本席接納羅女士在這兩方面的解釋。
羅先生稱在死者簽第三份遺囑時他是不在場的,他指該天上午他和葉女士去探望了死者後,下午並沒有再去醫院。卓女士卻指大女兒告訴她在大女兒到達後羅先生和葉女士曾到場。葉先生稱他沒有印象死者父母是在場。本席認為沒有足夠證據證明羅先生當時在場,並且羅先生是否在場並不重要。
葉先生並不是遺產的受益人。本席有機會觀察他作證時的神態。雖然他的證供和他的證人陳述書並不是完全吻合,譬如他在庭 中指死者是在2月18日致電給他時提及想見大女兒而非2月19日,但這些不吻合之處並不足以影響他主要的證供。
本席認為葉先生是一位可靠及中立的證人。他是羅女士及羅先生傳召出庭作證但並沒有足夠證據顯示他偏幫羅女士及羅先生一方。
譬如當羅女士知道葉先生欠死者款項時曾建議他將款項交給她去購買一項物業保值,直至大女兒 21 歲才交給大女兒。葉先生並不贊同羅女士該項建議。
本席認為這是葉先生明智之舉也表示了他的中立性。即使沒有醫師的記錄,本席接納葉先生有關死者立遺囑的行為能力方面的證供。本席認為羅女士及羅先生能夠證明到死者在簽署第三份遺囑時是有立遺囑的行為能力及他的精神、記憶及理解能力均為建全。死者是清楚、明白第三份遺囑的目的及內容。
本席並接納葉先生及羅女士的證供,死者在立第三份遺囑時是自己親自看過遺囑。他知道及贊同該遺囑的內容。死者是特意將財產遺贈於父母。
第二爭議點
卓女士在深圳的訴訟中曾指第三份遺囑為“代書遺囑”並指因羅先生及葉女士年事已高,而羅先生及葉女士百年歸老後羅女士將來是他們遺產的受益人,因此羅女士為死者遺產的“間接受益人”及葉先生為死者親屬,因此他們兩位不具備作為死者遺囑見證人的資格。卓女士指這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 18 條規定。
在深圳判決書中,深圳法院已指出第三份遺囑為合法及有效而卓女士對該份屬於“代書”遺囑的“主張”為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因此法院不予採信。
卓女士現正在上訴,因她似乎認為深圳法院認定該遺囑“不屬于代書遺囑”。無論如何卓女士一直沒有向本法庭呈交任何國內法律專家意見。
在考慮了卓女士所提供的證據,本席認為卓女士未能向本法庭提出足夠證據以證明第三份遺囑的形式(formality)令致該遺囑在國內為無效。
第三爭議點
卓女士曾在 2010 年 8 月 12 日作出一份聲名書指大女兒到達南山醫院後羅女士曾帶大女兒離開病房外一段時間,而當大女兒回到病房時是沒有看見葉先生簽署任何文件。卓女士因此質疑第三份遺囑不是在兩位見證人同時在場情況之下簽署的。
但葉先生堅持他和羅女士是同時在場見證死者簽名。他稱沒有任何印象羅女士曾否帶女兒離開死者房間。他指當時各人在簽名時大女兒並不是在他的視覺範圍之內並且大女兒可能在各人後面看不到他們簽名。
聲明書是卓女士本人所作,不是大女兒所作或簽名的。卓女士稱她堅信大女兒對她所述有關2月19日的情況。大女兒當時只有15歲。死者的房間並不是私人房,房間內有三張病牀。葉先生已提及簽遺囑時是“遮遮掩掩”因此明顯地他們是不欲大女兒看到。大女兒曾離開房間,大女兒看不到並不能證明死者不是在兩位見證人同時在場時簽第三份遺囑。
在考慮了葉先生及羅女士的證供,本席接納死者是在葉先生及羅女士同時在場見證下簽署第三份遺囑及每名見證人在立遺囑人面前作見證並簽署該遺囑。
不論如何,本席接納第三份遺囑的簽署是符合香港法列第 30 章《遺囑條例》第 5 條內所列的規定。
卓女士也曾質疑死者的居籍是香港或內地。死者在國內出生及受教育至高中畢業後移居香港。死者在他 2006 年的離婚呈請書中自己聲稱他和卓女士的居籍均為香港。他在三份遺囑中均自己宣稱他的居籍為香港。
據深圳市死者的死亡證及入院記錄,死者的戶口所屬及籍貫均為香港。即使在死者未申請離婚前,從他的2001年至2006年的出入境記錄中可看到他經常在羅湖過關。雖然後來他在國內的日子增多但他仍經常回港。
本席認為卓女士並沒有提出足夠證據證明死者在簽署第三份遺囑時居籍並非在香港。
結論
在考慮了本申請所有情況後,本席作出判令宣告第三份遺囑為有效的遺囑。
本席撤銷卓女士的申請及她在 2012 年 7 月 30 日所存檔的“知會備忘錄”。
卓女士須支付羅女士及羅先生在本申請中的訴訟費,如雙方沒有協議須由聆案官評定。此為一暫准命令,在 21 天後成為最終命令。
▄▊心得体会
1.本案的遗嘱类型属于打印遗嘱
打印遗嘱的形式要件,必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全程陪着办理。遗嘱打印出来后,遗嘱人和每个见证人都要在遗嘱的每一页上签字,并且在每一页都注明年、月、日,防止中间页被偷偷换掉。
2.法律对遗嘱人行为能力认定
我国《民法典》第1143条规定遗嘱人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有力,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要求立遗嘱人在意识清醒、意思表示真实且具备完全认知与判断能力的状态下,处分个人合法财产。
香港判例法规定,法庭是須考慮立遺囑人在立遺囑時是精神、記憶及理解能力的健全,有處置財產的健全心智和健全記憶。
3.遗嘱见证人资格认定
我国《民法典》第1140条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
(1)无民事行为有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
(2)继承人、受遗赠人;
(3)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
香港法列第 30 章《遺囑條例》第 9 條 遗嘱不因见证人没有资格而无效。见证人遗嘱签立的人,如于签立时或其后任何时间,没有资格获接受为可证明该项签立的见证人,该遗嘱并不因此而无效。
▄▊案例原型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遺囑認證訴訟 2011 年第 3 號 HCAP 3/2011
申请类型:遺囑認證訴訟
题目8
在香港,如何继承遗产
▄▊香港遗产继承
1.香港遗产继承的基本分类
香港的遗产继承分为:无争议的遗产继承,有争议的遗产继承。
无争义的遗产继承通过香港高等法院的遗产承办处来解决,有争议的遗产继承就需要通过诉讼来解决。
实务中,有遗嘱的,对遗嘱的效力等可能也会发生争议,导致要进入诉讼程序来解决。
而没有遗嘱要适用法定继承的,也未必就有是有争议的,当各继承人对财产的继承没有争议时,也可以走高等法院的遗产承办处,申请授予书来继承。
2.什么时候知道遗产继承可能会发生争议呢
在被继承人离世后,要对遗产进行分割时,继承就开始了。
如果各继承人争议很大,且没有办法调和,那大概率就是要发生争议了。
香港的遗产继承,中有一个预防的措施,叫做知会备忘程序。
《知会备忘》可理解为一份通知书,这份通知书需要在承办处登记,以确保死者遗产的授予书不会在没有通知知会备忘登记人(即登记知会备忘的人)的情况下发出。如果已有针对死者遗产的有效《知会备忘》,司法常务官就不可以发出授予书。《知会备忘》从登记日起计算,有效期为6个月,亦可再度登记。
一方向遗产承办处申请授予书,在申请的过程中,有人申请了知会备忘,接下来的程序可能会进入争议程序,也就是诉讼程序。
但是,双方也可以继续协商,排除双方的争议,之后继续来申请授予书,通过遗产承办处的颁发的授予书来继承遗产。
3.遗嘱认证人或遗产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非常大
(1)权利
全权处理遗产:收集、管理和处置死者位于香港的各类资产(如银行账户、房产、股票等)。在获得授予书前,任何人擅自处理遗产可能构成刑事罪行。
如果遗产受到侵害,是由遗产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作为代表诉讼的,遗产的受益人并不能够直接去主张。
代表遗产参与法律程序:有权以遗产代表人的身份提起诉讼或参与诉讼,以维护遗产的利益。
分配剩余遗产:在清偿债务、支付费用后,根据遗嘱的指定或《无遗嘱者遗产条例》 的规定,将剩余遗产分配给受益人。
(2)义务
妥善管理遗产:以谨慎、专业的标准管理遗产,避免不当行为导致遗产受损。否则,法院可能撤销职务。
清理遗产并清偿债务:首先查明并清偿死者生前所欠的税款、债务及丧葬费用等。
编制并提交遗产账目:应受益人要求,有义务提供遗产账目。若拒不提供或严重延误,可能面临法律挑战。
▄▊案例原型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 遗嘱认证诉讼2005年第6号HCAP6/2005 关于死者徐宗真之遗产事宜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 遗嘱检定裁决权知会备忘申请1998年第780号关于死者徐宗真之遗产事宜
题目9
撤销“遗产管理书”案
▄▊导语
在涉港家事继承案件中,当一份遗嘱“意外”出现,挑战已授予的“遗产管理书”时,法庭将如何决断?
本案正是一起围绕遗嘱真实性、立遗嘱人行为能力以及继承人诚信义务的典型纠纷。
通过剖析本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香港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的严谨逻辑与核心考量,尤其对程序合规性的高度重视,为处理类似遗产争议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
▄▊案件背景
本案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涉港遗产纠纷。
案件中的家庭,两夫妻育有三名子女,分别是大女儿、大儿子、小儿子。
父亲早年已经辞世,2018年4月14日母亲也过世。
夫妇二人生前置有两处物业,分别是位于九龙湾的“405物业”和“619物业”。
母亲过世后,2019年3月22日,大儿子向遗产承办处存档誓章,申请获授予遗产管理书,声称自母亲去世后,已尽力搜寻母亲档及财物,试图查究是否立有遗嘱,但最终未能寻获任何遗嘱。
基于此,法庭于2020年5月20日向大儿子授予了遗产管理书。
2020年8月4日大女儿作为原告,对大儿子提起诉讼,开展本案,小儿子亦作为证人参与本案。
▄▊攻防观点
大女儿即本案原告(下称原告)的诉求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要求撤销大儿子即本案被告(下称被告)于2020年5月20日获得的遗产管理书;
(2)请求法庭向原告授予遗嘱认证书;
(3)要求被告交付属于死者遗产中的所有资产、金钱及财产,并提供相应账目。
为进一步保障权益,原告方于2020年9月4日成功向法庭取得禁制令,禁止被告在本案审讯完结或法庭另有命令前,亲自或通过他人处置或处理死者遗产内的任何资产,或做出任何可能缩减遗产价值的行为。
审理过程中,被告方于2020年8月18日在法庭存档两份抗辩书,然而这些在2020年11月30日被法官认定不符合规范,不被当作恰当的抗辩书。
被告按照法庭要求于2020年12月18日再次存档了一份抗辩及反申索书。但是在2022年4月28日,许家灏聆案官下令要求被告在2023年3月9日前说明其是否管有、保管或控制与申请遗产管理书相关的档。
由于被告在期限内,未能做出回复,被告的第三份抗辩及反申索书最终被自动剔除。这一程序上的失误直接导致被告失去了出庭做供的机会,仅保留盘问原告的权利。
▄▊法庭查明
随着案件推进,法庭逐步查明了更多事实细节:
夫妇二人早年经营一家小型玩具工厂,在原告和小儿子的协助下,陆续购置了多个物业。2013年父亲去世后,母亲便与原告及小儿子共同生活。
2016年,死者被诊断患有脑肿瘤,经治疗后得以康复。2017年9月,死者要求大女儿为她订立遗嘱,并通过李国英律师事务所办理——这家律师行曾为其父亲草拟遗嘱,可谓渊源颇深。
2017年9月25日和2017年9月28日,死者在大女儿和小儿子的陪同下,先后两次前往陈律师办公室完成遗嘱的订立。
整个过程符合法律要求:死者在遗嘱上亲笔签名,陈律师和另一位见证人李女士也分别作为见证人在遗嘱上签署。
遗嘱订立后,2017年10月的一次家庭聚餐中,死者主动告知被告关于她已经订立遗嘱的事宜,并明确表示未在遗嘱中为其留下遗产,理由是她认为被告已经得到了他应得的东西,被告人在之前曾创办一门生意,并说服了死者一起参与,但后来他和死者的公司被告上法庭,败诉后,更被对方取得两项针对 619 物业的押记令,而该两项命令至今还未被解除。被告当时并未提出任何质疑。
直到母亲过世后的2020年7月,原告突然接到405物业和619物业租客的电话,得知被告竟向租客声称自己是这些物业的业主,并要求租客直接向其支付租金。
原告经查册后发现,原来被告获得的遗产管理书已被注册在这两个物业的土地登记上。小儿子随即于2020年7月3日致电被告,在通话中,被告声称该遗嘱系伪造。
▄▊法庭认定
经过详细审理,法庭最终选择采纳原告方的证供,认为其证人可信度较高,理由有三:
(1)证供在经过多番盘问后仍保持一致性,没有出现自相矛盾之处,且证人缺乏作伪证的动机;
(2)小儿子的证言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
(3)原告在作证过程中有机会以听到的小儿子的证词做出更有利于自己的证供,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坚持了陈述了事情,表现出充分的诚实可信度。
关于遗嘱签立环节,法庭认定其符合法律规定:
(1)死者系自行签署遗嘱;
(2)有两名合格见证人在场见证,完全符合《遗嘱条例》第5(1)条的规定;
(3)尽管没有录像记录整个过程,但这并不能反证遗嘱未妥为签署。
在遗嘱能力认定方面,法庭认为:
(1)遗嘱内容表面合理;
(2)在缺乏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推定死者具备精神能力;
(3)患有脑癌这一事实不能直接推定其不具有精神能力;
(4)尽管未完全遵循"黄金法则"——即安排执业医生在满意死者有订立遗嘱的能力即能理解遗嘱的内容后见证签署,但法庭明确指出:"黄金法则只是为律师提供了一种谨慎的指引,而并非一成不变的法律,不一定意味提呈遗嘱者不能成功证明立遗嘱人的订立遗嘱能力或理解遗嘱内容,一切皆视乎案件的实际情况。"
▄▊判令
基于以上认定,法庭作出最终判决:
(1)撤销被告人于2020年5月20日获得的遗产管理书(编号HCAG004697/2019);
(2)确认该遗嘱以严谨方式得到认证;
(3)要求在原告人完成所需手续及程序后,向其授予遗嘱认证书;同时命令被告人必须交付属于死者遗产中的所有资产、金钱及财产,并提供完整帐目。
此外,法庭特别指出,被告人明知死者立有遗嘱,却仍径自申请授予遗产管理书,这说明其当初获授遗产管理书时的誓词内容不属实。对此行为,法庭明确表示不满,并判定被告须向原告支付本案讼费。
▄▊律师心得
通过本案,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重要启示:
(1)关于遗嘱有效性的举证责任
提呈遗嘱者负有全面的举证责任,必须同时证明三个关键要素:遗嘱签署符合规范、立遗嘱人具备完全行为能力,以及立遗嘱人知情并同意遗嘱内容。
(2)律师见证中"黄金法则"与实务的平衡
本案再次凸显了遗嘱实务中的"黄金法则"的价值——建议律师在立遗嘱人年迈或患病时安排医生评估其精神状态并做好记录。但与此同时,法院也明确表示,未严格遵守该法则并不必然导致遗嘱无效。
在本案中,虽然律师未安排医学评估,但其见证过程符合规范,对遗嘱内容进行了充分解释,加之被告方未能提出任何反证,这些因素共同促使法院最终认可了立遗嘱人的能力。
(3)诚信义务与程序合规的重要性
本案被告在知悉遗嘱存在的情况下,仍以"未找到遗嘱"为由申请遗产管理书,被法院认定为不实陈述,并因此承担个人讼费。
这凸显了遗产承办人负有主动、诚信查询遗嘱的义务,特别是在非共同居住的情况下,更应积极与其他亲属核实情况。任何隐瞒或疏漏都可能引发后续诉讼,并带来不利的成本后果。
此外,从程序层面来看,被告两次存档的抗辩书均因不符合规范未被认可,第三次的抗辩书又因未能遵循法庭要求回答相关问题而被剔除,这直接导致其失去做供的机会。
在最后陈词中,法庭再次强调被告未按流程要求呈交证据,对其陈述的证据并不会接纳或处理。这些都充分说明香港法庭对程序严谨性的要求极高,任何程序上的瑕疵都会直接影响案件结果。
▄▊案例原型
香港特别行政区 初审法院
遗嘱认证案件编号 2020 年第21号
HCAP 21/2020 [2024] HKCFI 987
主审法官︰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暂委法官欧阳浩荣
审讯日期︰2023 年 12 月 21 日及 2024 年 3 月 22 日
判案书日期︰2024 年 4 月 12 日
题目10
香港遗产遗嘱认证案分析
▄香港遗产遗嘱认证
▄▊攻防观点
本案正是一起围绕遗嘱真实性、立遗嘱人行为能力以及继承人诚信义务的典型纠纷。
原告主张:
(1)遗嘱妥为签立,内容合理
(2)死者具备遗嘱能力,理解并同意遗嘱内容
(3)有律师见证并逐段解释遗嘱
(5)遗嘱内容反映死者对家庭现实的合理调整
被告抗辩:
(1)死者学历低,不可能频繁更新遗嘱
(2)原告强迫死者订立遗嘱
(3)无医疗报告或录像佐证遗嘱能力
(4)死者患有中度阿兹海默症,无遗嘱能力
▄▊法院观点
1. 遗嘱有效性成立
(1)遗嘱由专业律师准备并见证,形式合法
(2)内容合理,反映死者对家庭状况的现实考量
2. 死者具备遗嘱能力
(1)律师多次会面,未发现精神能力问题
(2)遗嘱内容清晰、目的明确
(3)被告未能举证证明死者无遗嘱能力
3. 被告抗辩不成立
(1)学历低不等于无能力订立遗嘱
(2)强迫订立遗嘱的指控无具体证据支持
(3)医疗报告未证实死者有影响遗嘱能力的疾病
▄▊律师解读
1.遗嘱认证的关键要素
(1)形式要件:符合《遗嘱条例》第5条
(2)实质要件:遗嘱能力 + 知情同意
(3)举证责任:主张无效方需提出具体、可信证据
2.实务建议
(1)律师在订立遗嘱时应记录客户精神状态及理解过程
(2)若客户年长或健康不佳,建议安排医疗评估
(3)抗辩须具体、有据,空泛主张无法阻却简易判决
▄▊案例原型
高院遺囑認證訴訟 2023 年第 38 號
▄香港遗产遗嘱认证案
(遗产争议中的讼费命令与程序挑战)
▄▊攻防观点
1.原告方立场
(1)通过简易判决申请,成功获得遗产管理权
(2)要求被告人支付讼费,理由:被告无合理抗辩
(3)未对传票提出额外讼费申请
2.被告方立场
(1)通过传票主张“拒绝支付讼费”
(2)在誓词中认为讼费应由原告承担
(3)试图挑战原判决的实质内容,认为判决错误
▄▊法院观点
法律原则引用:
1.根据《Hong Kong Civil Procedure 2025》第42/5B/1段:
“更改暂准命令的申请不得用于覆核实质裁决,挑战实质裁决须通过上诉程序。”
2.法院认定:
(1)被告人申请基础错误,实质是质疑判决而非讼费命令
(2)未经许可提交的誓词不予考虑,且无新论點
(3)被告人程序不当,违反法律原则
3.裁决结果:
(1)撤销被告人传票
(2)暂准讼费命令转为绝对命令
(3)就传票无讼费命令(因原告未申请)。
▄▊律师解读
1.暂准命令的更改申请须严格限于程序问题,不可涉及实质裁决,无律师代表当事人易犯程序错误,需加强法律意识。
2.异议实质判决必须通过正式上诉渠道。
▄▊案例原型
高院遺囑認證訴訟 2023 年第 38 號
题目11
遗嘱认证有效的步骤
▄▊攻防观点
本案是关于死者的遗产,涉及遗嘱认证诉讼。
原告为死者的儿子,是死者唯一的子女,被告人是死者的第二任妻子和原告人的继母,被告人提出反申索书。
2019年5月2日死者因脑出血去世。
1.原告(儿子)的申索事项:
(1)授予被告人有关死者的遗产管理书予以撤销;
(2)以严谨的方式认证日期为2018年6月4日死者最后的遗嘱及授予原告人遗嘱认证书;
(3)申请剔除被告人的反申索。
2.被告(继母)的反申索事项:
死者所有资产归她名下及要求精神赔偿共90万港币及其他费用等。反申索理由:
(1)她相信遗嘱为原告人的笔迹;
(2)死者与原告人的关系建立在出世纸,及原告人性别为女性而遗嘱中提示的“儿子”与事实不符,因此遗嘱无效;
(3)原告人和她伴侣的行为可疑;
(4)于2016年圣诞至2017年新年死者的精神状况愈下;
(5)原告人为首,她的伴侣和死者的姐姐参与死者死亡阴谋。
▄▊死者遗嘱
2018年6月4日,死者在律师见证下,签立了遗嘱:
(1)死者委任原告人作为遗嘱的唯一执行人和受托人;
(2)死者把其银行现金和股票的45%遗赠被告人,45%遗赠原告人,10%遗赠原告人的妻子;
(3)死者把其金银珠宝遗赠原告人的妻子;
(4)死者把某公寓19A遗赠原告人和被告人,两人以分权共有方式各持一半份额;
(5)死者把某公寓9B单位遗赠原告人;
(6)死者把剩余财产平均遗赠予原告人和被告人。
▄▊相关法条
香港法例第 30 章《遗嘱条例》第 5 条列出如下
5、遗嘱的签署及见证
(1)除第6条另有规定外,遗嘱须符合以下规定,否则无效
(a)以书面订立,并由立遗嘱人签署,或由其他人在立遗嘱人面前并依其指示签署;
(b)看来立遗嘱人是欲以其签署而令该遗嘱生效的;
(c)立遗嘱人是在2名或2名以上同时在场的见证人面前作出该签署或承认该签署;及
(d)每名见证人在立遗嘱人面前(但不必在其他见证人面前) ——
(i)作见证并签署该遗嘱;或
(ii)承认其所作的签署,
但无须符合任何见证的格式。
(2)任何看来是体现立遗嘱人遗愿的文件,即使未有按照第(1)款所述规定订立,但只要有人提出申请,而法庭在无合理疑问的情况下信纳该文件是体现立遗嘱人的遗愿的,则该文件须当作已妥为签立。
▄▊法院观点
主张遗嘱为有效的一方有责任举证在平衡各种可能性后,以下事项:
(1)遗嘱乃妥为签立(第一项事项);
(2)遗嘱人具有订立遗嘱的能力(第二项事项);
(3)立遗嘱人知道并同意遗嘱的内容(第三项事项)。
针对以上事项,原告举证,法院进行一一审查讨论:
(1)就第一项申请:遗嘱妥为签立
根据上述香港法例第 30 章《遗嘱条例》第 5 条,本案遗嘱以书面订立,并有两名律师同时在场见证死者签署遗嘱。且被告人不能提出任何证据证明遗嘱为伪造或为原告人的笔迹。
因此法院认为遗嘱符合《遗嘱条例》第 5 条的各项要求。
2.就第二项申请:死者订立遗嘱的能力
原告人提供了死者自1994年起就经常咨询的私家医生出具的报告,显示死者一直思维清晰,除了心脏问题,并无其他常规疾病。
两名律师亦提供证词,证明在与死者沟通遗嘱事项以及签订遗嘱会面时,沟通流畅,相信死者精神正常,具有订立遗嘱所需的能力。
遗嘱的内容合理,被告作为死者妻子的得到现金和股票的45%,19A单位的一半份额及剩余财产的一半。
因此,法院认为被告人的说法不可能推翻死者具有订立遗嘱的恩能力,法院认为死者有订立遗嘱的能力。
3.就第三项事项:立遗嘱人知道并同意遗嘱的内容
上述已指出及认为遗嘱乃妥为签立及死者拥有订立遗嘱能力,这可以推定死者知悉及认可遗嘱的内容。并且遗嘱由专业且独立的律师预备,并由律师向死者解释了遗嘱的内容,死者明白并在遗嘱上签署。原告人早于2007年更改性别,因此死者于遗嘱中提及的儿子明显是指原告人,这不是与事实不符。
因此法院认为被告人的抗辩并无任何可审理的争议点,被告也不能证明她的案情是可以信赖的,反申索没有任何理据,予以剔除。
综上,法院批准原告人的两项申请:
(1)授予被告人有关死者的遗产管理书予以撤销;
(2)以严谨的方式认证日期为2018年6月4日死者最后的遗嘱及授予原告人遗嘱认证书。
▄▊心得体会
1.主张遗嘱为有效的一方负有举证责任,主要关于以下事项:
(1)遗嘱乃妥为签立;
(2)遗嘱人具有订立遗嘱的能力;
(3)立遗嘱人知道并同意遗嘱的内容。
2.在有遗嘱指定死者儿子为唯一遗产执行人的情况下死者配偶还可以申请遗产管理书?
遗嘱中委任了儿子作为遗嘱执行人,配偶一般不能申请遗产管理书。只有在遗嘱执行人去世、放弃权利或者因其他原因不能或不愿意履行职责时,配偶才可以申请遗产管理书,但必须向遗产承办处提交有关遗嘱执行人已死亡或放弃权利的证据。
根据香港法例第 10A 章《无争议遗嘱认证规则》,申请遗产管理书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申请人具有相应资格
如果死者未立遗嘱,或者遗嘱中未指定遗嘱执行人,或者遗嘱执行人无法履行职责,那么根据法律规定的优先次序,有权申请遗产管理书的人士包括死者的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姊妹等。
申请应由享有较高优先权的人士提出,如果享有较高优先权的人士已去世或放弃获得授予书的权利,则享有较低优先权的人士有权获得授予书。
(2)符合人数和年龄限制
a.授予书不得发给超过 4 名人士;
b.如果遗产涉及未成年的受益人及 / 或享有终身权益的人,则授予书必须发给不少于两名人士;
c.授予书不得发给未满 21 岁的人士。
本案中,原告人向继母出示了遗嘱,但继母还是申请了遗产管理书且拒绝撤销遗产管理书,因此原告人才向被告人开展本诉讼。
(3)遗产执行人的权利救济
香港高等法院对所有与死者遗产的遗嘱认证及遗产管理有关的事宜,均有司法管辖权,并有权对死者遗产授予遗嘱认证及遗产管理书,以及有权更改或撤销该等授予。
如果遗产管理书的授予不符合法律规定,例如另一继承人在遗嘱执行人未去世、未放弃权利且有能力履行职责的情况下申请并获得了遗产管理书,遗嘱执行人可以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撤销该遗产管理书。
▄▊案例原型
HCAP 45/2019
[2021]HKCFI 1120
案由:遗嘱认证诉讼
题目12
十年遗产管理案的僵局
▄▊案件背景
本案为一宗典型的无遗嘱继承遗产管理权纠纷。
死者王时德于2012年6月离世,未立遗嘱,留下估值约1700万港元的遗产,主要包括美孚新邨及荃湾的两处物业、股票及银行存款。
死者家庭关系复杂,其七名子女分别为原配与继配所生,并在本案中分化为两个阵营。
尽管第一被告人(王曙)与第二被告人(王贤庄)早在2015年经法院同意命令被委任为共同遗产管理人,但由于家庭成员间积怨已深、互信全无,遗产管理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陷入完全停滞,甚至连遗产管理书都未能领取。
争议焦点:
2019年,原告人(王贤琨)提起诉讼,要求撤换原有管理人并由自己担任唯一管理人,其余两方亦分别提出反申索,均主张自己为最合适的唯一管理人,案件最终进入正式审讯。
▄▊攻防观点
1.原告人的主张
(1)指责第二被告人以合資为名,骗取死者23.3万港元用于购买美孚12C单位;
(2)指控第二被告人单方面更换并霸占美孚33物业,拒绝交出钥匙。但同时对第一被告人可能操控“暗遗产”的问题态度暧昧,甚至在录音中讨论如何隐匿财产;
(3)其自身亦被揭露曾教唆第一被告人用技术手段锁门,行为有失公允。
2.第一被告人主张
(1)指控第二被告人一方成员曾对其有人身安全威胁(如推落海事件);
(2)坚持第二被告人必须先交还美孚33钥匙,方能推进管理。
(3)同时否认存在“暗遗产”,但在第二被告人提供的秘密录音中,其明确承认有“只有得我一个人去知道”的“不明確”部分遗产,与其庭上证词严重矛盾,可信度受损。
3.第二被告人主张
(1)核心指控第一被告人隐瞒并意图侵吞“暗遗产”,并出示死者日记与秘密录音作为关键证据;
(2)指控第一被告人进行恐吓及原告人协助非法禁锢。同时就其获得的23.3万港元款项,未能合理解释死者日记中“⅙”份额的记录;
(3)其私自录音、单方面换锁等行为,亦被法庭认定为关系破裂、互信缺失的明证。
▄▊法律适用
本案的法律争议核心在于:在何种情况下,法院可以撤换已委任的遗产管理人。
香港法例第10章《遗嘱认证及遗产管理条例》第33条。该条规定,法院如信纳“为妥善及适当管理该遗产及为实益享有该遗产的人的利益而有所需要”,可将遗产管理人撤职并委任替代者。
法院援引了大量权威判例与法学著作(如 Williams, Mortimer and Sumnucks),明确了以下关键原则:
(1)撤职无需以不当行为为前提;
(2)管理的有效性及实益享有人的福利是最高考量;
(3)法庭有权委任独立的专业人士(如执业律师)担任遗产管理人,以确保公正与效率。
▄▊法院观点
1.法庭并未试图对所有的陈年旧怨(如推落海事件)或实体争议(如“暗遗产”的确切构成、美孚12C的权益)作出终极判断。
相反,法官聚焦于一个无可争议的核心事实:三方关系已完全破裂,互信尽失,导致遗产管理在过去未得进展。
2.颁令撤换第一及第二被告人并进一步指出,七名子女中无一人适合担任管理人。因此,委任一名独立的执业律师为遗产管理人。
法院后续在(第二号)判案书中,因仅第一被告人按要求完成了推荐程序,最终委任其推荐的律师为单一遗产管理人,并设定了受法规上限约束的薪酬标准。
▄▊心得体会
1.香港法院在此案中展现了其普通法体系的灵活性,“关系破裂”作为关键撤换标准,与内地《民法典》更侧重于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损害而追究责任不同。
2.本案委任独立专业人士处理复杂家庭纠纷,虽产生额外费用,但能有效搁置争议、推进程序,从根本上保护遗产的价值和全体继承人的长远利益。
▄▊案例原型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高院遺囑認證訴訟
編號 2019年第6號
HCAP 6/2019
[2022] HKCFI 2785
根据表格内容,香港与内地法定继承规则的主要差异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1. 继承模式不同:香港侧重保护配偶权益,采用“固定份额+剩余分配”模式;内地则严格区分两个继承顺序,强调均分与赡养义务。
2. 继承顺序灵活度不同:香港不严格区分顺序,按亲属类别组合分配;内地则明确分为两个顺序,配偶、子女、父母为第一顺序。
3. 配偶继承权差异明显:香港配偶在不同亲属组合下享有优先继承固定金额;内地配偶与子女、父母在同一顺序中均分遗产。
4. 特殊人群照顾各有侧重:内地明确规定对困难继承人、尽扶养义务者可多分,并保留胎儿份额;香港则更注重配偶与近亲属的财产分配。
❖